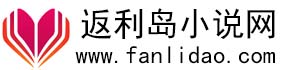40-50(18/26)
出了问题。”“东边的海盐吗?”张沁沁绞着手中的帕子,“听说东瀛人常来叨扰海面的居民,不知道——”
“殿下,再不吃的话菜就冷了。”眼看着这般聊下去大有聊个不停之势头,王阿花用筷子敲着碗提醒道。
政务是聊不完的,可是饭要是不吃的话就冷了。
许言锻朝着张沁沁碗里夹了一大块,张沁沁虽还是没有同旁边的人搭话,但还是略微吃了碗中的菜两口。裴安懿接过王阿花盛的鱼汤,小口小口地喝着。
两壶热酒下肚,王阿花微微有些发汗了,许言锻也用着袖口擦着汗,张沁沁见了,从怀中掏出一块帕子掷给旁边的人,许言锻接住,反是一呆。
“擦吧,回头洗干净了还给本小姐。”
王阿花闻言掩面而笑,遭到了伶牙俐齿情场失意的张沁沁小姐一记白眼。
又是两壶热酒下肚,浑身发汗,许言锻用手肘轻轻推了推王阿花,王阿花福至心灵,知道这家伙满足了酒瘾就犯了武瘾。转身取下长剑,同裴安懿眨了眨眼,便同许言锻出去一道切磋了两招。
外面大雪扬扬,王许俩人比武切磋点到为止,刀剑相交,大雪落下,两人的身影恣意飞扬。
裴安懿倚在窗边上,拢了拢身上的袍子,靠在窗边,望着窗外矫若游龙的两人,扬了扬嘴角。忽觉心角一痛,微微蹙眉,不动声色地揉了揉胸口。
“殿下,”张沁沁走上前来,这四年裴安懿的身体虽常人见着虽没什么,她却是清楚怕是出了些状况。
话还没说出口,便被裴安懿打断道:“无碍,老毛病了。”
……
长安大雪封路,天色已晚。
王阿花拨弄着暖阁里的炭火,炭火发出微微皲裂之声,烛光昏黄,暮色沉沉,叫人困乏,王阿花幽幽打了个哈欠。
她实在是困得紧,但除夕夜裴安懿好像还没有睡觉的意思,她穿着单衣,披着外衫,不知道从哪里忽然拿过来一张涂着鬼画符的宣纸,摊开在桌案上。
“什么啦?”王阿花将头凑了过去,“殿下大冷天的不睡觉,怎么突——”
王阿花将“突”字拖得又尖又长,在看清这张宣纸上的内容之后又戛然而止,这张宣纸上的“鬼画符”她眼熟得很,不是她的字迹还能是谁的。
“真难看诶。”王阿花笑着吐了吐舌头,将纸拿了起来。
“不难看。”裴安懿拍了拍怀中人的头,“初学写字的人大多都是这样的。”
“是吗?”王阿花抬起头,“那——殿下现在写得一手好字之前,也有着‘鬼画符’的时候吗?”
裴安懿笑而不答,反而转移话题问道:“你可看出来这纸上写的是什么?”
“明知故问。”
纸张上是她往年在长公主府里初学写字时的“大作”,闲下来的时候她喜欢随便写写,一不留神“裴安懿”这三个字就密密麻麻地填满了一整张纸。王阿花将头埋进她家殿下柔软的小腹上,在裴安懿身边缩成一团,“不过殿下,你是什么时候发觉的呀?”
“发觉什么?”
“嗯……就是,发觉、发觉那个——”
裴安懿垂眸,“假死吗?”
埋在身下的人缓缓点了点头,又闷声说,“是不是张小姐告诉殿下的?”
裴安懿向后挪了挪,换了个姿势,确保底下的人能在自己腿上枕得更舒服,柔声说道:“非也,重逢的第一面,我约莫就认出你来了。”
“那日刺杀,你虽将自己遮得严严实实,但一招一式,我都认得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