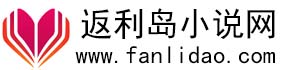22-30(17/24)
那间属于我的卧室。仿佛逃离的念头从一开始就种在我的心里。”时归眉头紧皱, 回忆逐渐变得痛苦,“对于我的父母,我也没什么印象了。”“我知道我的母亲很多年前就去世了, 父亲也不常回家。”时归想得有些费力,额头上逐渐涌出一层细汗,“或者说,我住的房子并不是我父母的家。”
“屋子里有我,有保姆,还有,”时归停顿了许久,下定决心才终于坦白,“还有一只夜莺。”
夜莺。
聂徐川猛然抬头,正是在阿瓦对时归的这句称呼的刺激下,时归扣响了扳机。
“他为什么会这样叫你?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时归呼吸急促起来,回想起那个场景仍然让他汗毛直立,仿佛触发了身体里的某个开关,“他让我很不舒服,感觉就像,就像回到了小时候。”
“对不起,聂队。”
聂徐川抬起另一只没受伤的手,轻轻擦去他额角的汗水,一时间无言。
“我可以相信你吗,时归。”聂徐川偏头不看他,眼神远远落在医院小花园中央的喷泉上,飞溅的水花明明咫尺就要逃离桎梏却在空中狠狠跌落,再次化作池中之物。
“如果你想要把我交给市局调查,或者去省厅,我没有意见。”
阳光分明很好,但四周很暗。大门关闭的吱呀声沉重而诡异,远处传来几声夜莺的低鸣,时归缓缓睁开眼,一切却又消失不见。
聂徐川长久地沉默着,他知道此刻最正确的做法是全盘托出,时归会立刻接受调查,不论是市局还是省厅,会有审讯专家、心理医生轮番上阵,迟早会从时归口中得出一个似真或假的答案。
回过头去看了一眼时归,他侧坐在花园的长椅上,显得十分疲惫,任何对于过往的回忆于他而言相当一场酷刑,是绵密而持久的疼痛。
瘦削的身躯不知背负着何种沉重,他的脊背仍旧挺直。低着头,脖颈处露出优美的弧线。
聂徐川也知道,如果时归真想被审讯,他不会选择在这个时机向自己坦白。
他在赌。
苦笑一声,聂徐川捂住脸,“时归,我算是输了。”——
“由于情况危急,犯罪分子阿瓦仍然存在战斗能力,时归同志不得已向他开了一枪,可惜没有打中。”
聂徐川面不改色扯着谎,安副局臭着脸听。
“你小子,虽然我说了让你带着他点,但是这么危险的抓捕行动你也要带上时归?”
“对不起,是我的疏忽。”
“没有下次了。”安副局摆摆手,“阿瓦死了,死前对于之前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,你们写个报告结案吧。”
“安副局,我认为是时候重启十二年前爆炸案的调查了。”聂徐川的手还肿着,打着石膏吊得老高,“阿瓦死前喊的话,您也听到了。”
安副局挪动了两步,一屁股陷进了沙发里,“牵一发而动全身,没有足够的证据,上面不会轻易同意重启调查。”
“这件事情,是整个公安系统的痛,没有动机、没有线索、没有结果。参与了行动的同志死的死伤的伤,好不容易活下来,还要被当成内鬼摸排,阻力很大。”
聂徐川刚要争辩,却又被安副局打断:“我知道你很急,但是你先别急。我让你们注意牙齿,也是一种默许。背后的始作俑者迟早会露出端倪,在此之前敌在暗我在明,所以办案要知道变通。”
聂徐川明白了安副局话里的深意,隔着茶几应了一声。
“还有,你个半残查个屁查!”安副局冲这聂徐川包成猪蹄的手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