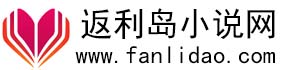50-60(26/39)
的母亲, 纵使死亡在人心中是首当其冲。奚吝俭并非逼着苻缭提及伤心事,只是觉得苻缭不该什么都不说。
他也知道,自己清楚他们府上的事。
还是说……真正的“他”, 没有什么可以告诉自己的?
被埋没在心底的想法重新冒了出来,迅速破土而出,顶至他的胸膛。
从无端转变的性子开始, 他便觉得怪异,只是当时觉得凭眼前这人的模样又是做得出来, 才认同了他这说法。可现在想来,确实有太多不足之处。
但眼前这人做了这么多吃力不讨好的事, 又图什么?
奚吝俭越来越看不透面前的人。
他的眼眸虽然清澈, 可看久了, 便觉得太过清澈, 让人生出冰凉彻骨的寒意。
又像是糅杂了各色的黑,黑得极致, 什么都融为一体,反倒显得清澈和谐。
奚吝俭觉得,这两种都不是苻缭。
他见过苻缭眼底下的灼热,即使只是一闪而过。
苻缭却从没说过。
是他自己不知道,还是单纯地不想和自己说?
奚吝俭不去猜测,他直接问道:“有什么能和孤说的?”
苻缭看着他的眼眸,眨了几下,躲闪似的目光从他双眼溜走,滑过他的棱角分明的下颚线,他的喉结,还有他挺拔的脊背。
但他不敢再看奚吝俭的眼睛。
他怕从里面看见对自己的失望。
苻缭心脏猛然抽痛一下。
他不是没有可以说的事。
只是这些事情,尽数和奚吝俭有关。
告诉他,我能够分享的事和人,都是你。
只有你。
他怎么能开得了口。
苻缭瑟缩着,像是受惊的小兽,仍旧死死咬着牙,意图迷惑企图猎杀他的天敌。
奚吝俭见他沉默,知道了他的意思。
他忽然感觉万分疲乏。
两人挨得很近,只要活动一下身子,都能挨着对方。
奚吝俭许久没有这么长时间地与人这样待过,几乎可以说是促膝长谈。
苻缭不抵触他们离得近,似乎只是因为他不在意。
奚吝俭并不是觉得这不值得,只是胸口突然疼了一下,像被敌人用尖□□进心脏。
“无妨。”奚吝俭最终站起身,“那就先这样吧。”
“等等!”
苻缭连忙去拉他的衣袖,可那些丝织却灵巧地避开了他的手,他连丝织的触感都没碰到,奚吝俭已经走出去了一段路。
苻缭立即起身要追,可久坐后的突然站起让他眼前瞬间一白,头晕目眩地找不到方向。
他的腿一软,直接摔在原地。
他顾不及去疼,撑起身子,以最快的速度把奚吝俭重新拉回自己的视线内。
“殿下!”
苻缭努力让自己视线变得清明,可看见奚吝俭最后一眼的身影,是他略略地侧目。
他甚至没看清奚吝俭的神情。
苻缭还想再追,但后知后觉的剧痛让他心有余而力不足,只能捂着伤处小小地喘息。
磕到膝盖了。
里裳被血液稍浸湿了些,好在外裳是披肩式,刚好能遮住残破的衣裳与底下的伤口
痛感逐渐蔓延,尖锐的麻木感让他不得不停下来缓两口气。
苻缭看着自己指尖沾上的鲜血。
红得很刺眼。